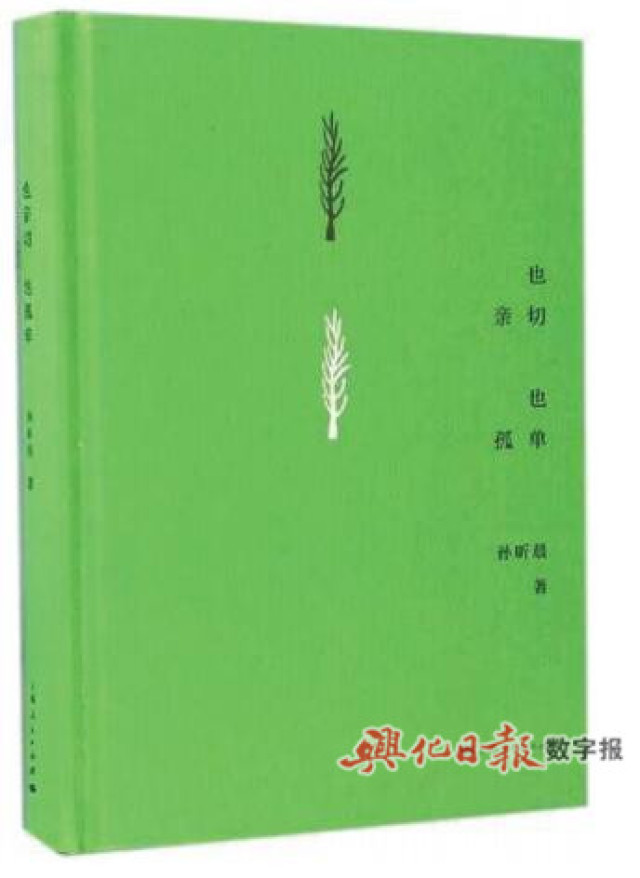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世界
——读孙昕晨散文集《也亲切 也孤单》
□宗崇茂
坐在这样一个夜晚,此刻我的内心绿意盈盈,因为我正读着一本散文集《也亲切 也孤单》。它淡绿色的封面和封面上的图案,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原野上的树,想起自己内心曾经的大片荒芜以及被重植、被引领的那段西部岁月……
高原土层薄,雨水少,大树往往难以存活。加之高原长年无尽的风雪,我的视野常常茫然一片。平原长大的孩子,缺少了大树的提醒,就像突然失去了方向。幸运的是,那三年中,我这个“荒凉中的孤儿”因为一棵树的指引,慢慢找到了方向。在无垠的戈壁荒漠中,不知有过多少这样的时刻:劳顿之余,有意无意地,我会突然抬头远望,朝向东方。那里是旷野的尽头,那尽头仿佛站立着一棵树。我守望着它,它也守望着我,给我祝福与启示,提醒我用文字记下每天所经历的一切,感受那降临于身的苦难而不使它白白流失,否则,真是一种罪过。这守望虽隔着数千里,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视野之内,从而引领我最终找到了一条回家之路。
这棵树的形象,就是《也亲切 也孤单》这本书的作者、被我视为文学兄长的孙昕晨先生。
这是文学给我带来的机缘与福分。而得到类似机缘与福分的远不止我一个。书中“凝望”那一辑中所收录的序文,就可见证昕晨对文学朋友们的相扶与相惜之情。上世纪80年代末,昕晨就享誉国内诗坛,一直在媒体工作的他,帮助过的作者难以计数,至今很多读者仍珍藏着他亲笔写去的信函。这种帮助是一个点火的过程,播种的过程。
从第一本诗集《雪地上的音乐》到散文集《也亲切 也孤单》,期间相隔了20多年,对于众多喜爱他文字的读者和他曾经的“江湖地位”来说,这漫长的等待未免过于“残忍”。期间,我也曾多次抱怨并催促过他出书的事。但后来又慢慢理解了他——面对当今这个泥沙俱下、人心浮躁的时代,他宁愿选择语塞和下沉。他对文字怀有深深的敬畏,以便让自己时刻保持着一种“清洁的精神”。虽然读与写从未停歇过,但他更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献给那“无限的少数人”。
“故乡、自然”是昕晨写作中的两个关键词。客居异乡20年的他,其实是一个从未真正离开过故乡的游子。家乡的田畴河流、庄稼草木,一直是他最大的滋养;远方的亲朋故友、乡间草民,是他最为亲切而又揪心的系念。而自然万物之生命——淙淙流水,落叶簌簌,唧唧虫鸣,都是他所酷爱和痴迷的。世事沧桑,唯有自然能够让人永葆新鲜。读他的《四季茫茫》和《感受大地的心跳》等篇章时,我一直猜测,在精神上,昕晨是以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和中国散文家苇岸先生为师为友的吗?
昕晨有一个网名叫“北”。为何以此为名?他在他的文字中似有回答——“我精神的罗盘永远指向北方。”北方那辽阔的黑土地、苍郁的大森林、冰雪下面那不事喧哗的河流,都令他感到一种“凛然爽洁的精神”!
“阳光下,丝丝缕缕的寒春风吹过,一个外乡人在旷野里想起了母亲,他朝着天空下的北——北——北……整整一个春天,他被方向感动着,他的心脏献给了远方的天空。”
读到这段时,我仿佛听到了高天之上一只孤雁的鸣叫,仿佛看到某个春天的黄昏,作者树一样伫立于旷野之中,他面向北方,想起了自己低矮朴素的村庄和白发苍苍的母亲。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几乎就喻示了他(她)个人的生活阅历或精神指向。
无论阅读还是做人,昕晨非常喜欢那些“有意思的人”,他也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生活中,朋友们常常感受到他的丰润与有趣。但作为他的好友,我似乎更敏感于他丰茂中的那份荒凉、亲切中的那份孤单。有一次,在无锡他家中的书房,面对整整三面墙的心爱之书,他说:“唉,想想这些书真是可怜,有一天我不在了,它们怎么办呢?儿子在国外,不需要它们,捐赠了吧,又不放心,这些亲爱的小伙伴,会有人疼你们吗……”那一刻,我只能呵呵一笑,笑他瞎想,笑他想得太早,但很快,我体悟到他内心的那份孤单——而这孤单,又是由他所热爱的事物带来的。作为一名诗人,也许拥有植物般的丰富触须,但那根叫做“痛苦”的触须似乎最为敏锐。在他多年前寄给我的未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有这样一首诗——
有时候天黑了我才点灯
有时候点了灯,天反而更黑
……
生活教会一个男人沉默
他的黑暗在走
点了灯,反而更黑,人堆里,却更孤单。在黑暗中走,与白天的狂奔完全反向,只是为了“与另一个自己告别”。这是一个思想者的彷徨与求索,也是一个诗人的自省与幸运。乔治·吉辛说:“上天对每个人都下了指令:你必须单独地生活。”所以说,被很多朋友视作“大哥”的昕晨,在我眼里又是一个“孤单的孩子”。这样一个孩子,拥有清澈的心地与童眸,能在喧嚣之中倾听到寂静,在繁华背后看见那荒凉。
昕晨的文字常常让我嗅到别样的气息——那是乡村早晨收割后的田野上,丝丝缕缕飘散着的露珠的清新与庄稼的成熟气息。这也是一个优秀诗人私奔于散文园地后给读者留下的“福利”。布罗茨基说:“人们不知道当诗人转向散文写作时诗歌蒙受的损失,但是,散文因此大大受益却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书中的最后一辑“活着的证据”。这其中的文字,分明是一个人孤单的结晶体,黑夜的孩子,尘世的喘息声;是阳光透过大树锻打出的碎金,也是一道又一道无法修改的闪电。
我想,昕晨骨子里是一个具有浓郁古典情怀的写作者,他从不刻意标新立异,但又从没放弃求新求异。他的文字之所以经得起反复阅读,当然与其文字中真挚自然的情感魅力分不开,但我想,也与他一直注重语言的“陌生化”分不开——普通的词语经过他的排列组合,往往能产生某种难以言传的奇妙效果。请看这段——
向黎带着我们来到一首诗面前,念出了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于是我们得以凝视五律七绝的眼睛,得以呼吸到平平仄仄的清新空气,得以从某个朝代某个诗人的诗句里听到另一个朝代另一个诗人的回声。我们的心情终于押上了唐代那个著名月亮的韵脚。于是,在某个夜晚,我们成为一首唐诗的小小注脚。(《那些花儿,你要商量着慢慢开啊》)
多么新鲜,多么独特!一段关于古典诗词的解读,在他的笔下有了别样的生趣。
昕晨是一个具有赤子情怀的作家。近些年,我们曾一同到过湘西、东北等地旅行。在沈从文先生的墓地前,我们虔敬跪拜(而他是第三次来到这里!);那一次我们去参观萧红故居,正遇闭馆,他虽是第二次来,但为了让第一次来的我不留下遗憾,他坚持不懈地打了很多个电话,一直追到哈尔滨市相关部门的领导,以自己的才与情打动了对方,最终放行让我们单独参观。他多次和我谈起过当年寻访木心先生并与之交谈的种种细节,对先生的敬爱之情,深藏于心。他的那些旅行,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内心方向的个人行走。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是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亲切 也孤单》,就是孙昕晨的个人心灵史,是“岁月的手印和时间的收据”,其中的亲切与孤单,都是读者可以分享与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