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散木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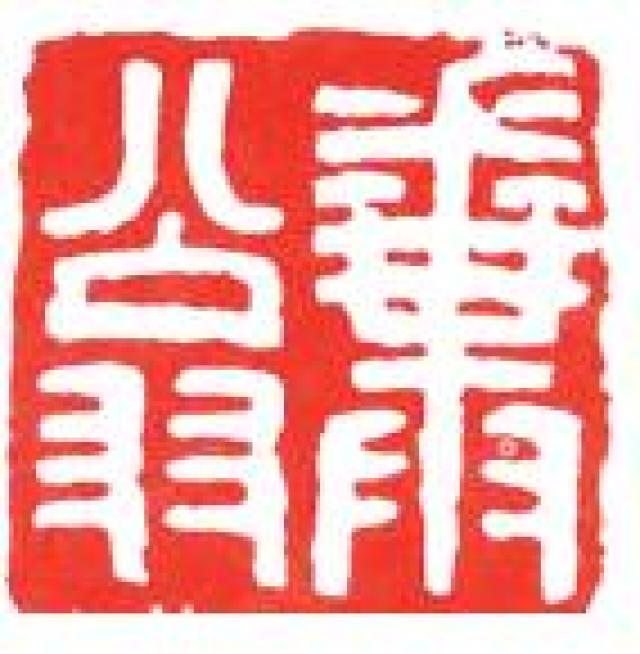
■/杏 仁
粪为污秽之物,清高孤傲、落拓不羁的邓散木偏却自称“粪翁”,榜其斋为“厕简楼”,刻印“遗臭万年”“海畔逐臭之夫”“不可向迩”“粪土之墙不可圬也”钤于得意之作。据传,邓散木幼年就读于教会学校,有一次,英国校长无端责备他,还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他深以为耻,视为“佛头着粪”,愤而退学。别号“粪翁”盖抒其愤懑之气也,亦寓“荡涤污秽”“视金钱、权贵如粪土”之意。
以粪入药古已有之,曾经赋予屠呦呦灵感的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中记载:“绞粪汁,饮数合至一二升,谓之黄龙汤,陈久者佳”,人中白(又名淡秋石,秋白霜,凝结在尿桶或尿缸中的灰白色无晶形之薄片或块片)、人中黄(又名甘中黄,甘草末置竹筒内,于人粪坑中浸渍一定时间后的制成品)也都是良药;还有动物粪便,如:两头尖(母老鼠)、白丁香(麻雀)、蚕砂(家蚕)、望月砂(野兔)、鸡屎白(家鸡粪便上的白色部分)、夜明砂(蝙蝠)、左盘龙(鸽)、五灵脂(寒号鸟)、龙涎香(抹香鲸)等。这些雅称有利于提高患者服药的顺从性。
以粪治病,常常被诬为歪理邪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当作糟粕而批判。然后,当我们屡遭“粪青”嘲讽的时候,国外却能信奉“疗效为王”,于1958年开始探索粪菌移植。2013年8月出版的《Science》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粪便的希望》的文章:一位81岁女性尿路感染患者,经抗生素治疗后,肠道菌群紊乱,导致艰难梭菌感染,产生严重的腹泻症状,伴褥疮、高热,不能进食,奄奄一息。医生借鉴以住的经验,勇当“粪翁”,将其健康儿子的粪便与0.9%氯化钠溶液的混合物通过鼻饲管注入患者的十二指肠,以期重建具有正常功能的肠道菌群。结果,治疗3天,奇迹般痊愈出院。
美国《时代》杂志和克里夫兰医学中心将粪菌移植选入“世界十大医学突破”之列。据统计应用粪便移植可以治疗腹泻病、肠易激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慢性便秘等消化系统疾病,还有代谢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多发性硬化症、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自闭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将粪菌移植纳入研究型新药管理。有学者认为粪便移植当做药物来管理还不够,肠道微生物群是人体另一个“隐藏器官”,而且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应该以人体组织来看待。粪菌移植是一种特殊的器官移植,且人粪菌群是人类可以真正共享而不会发生免疫排斥问题的器官。
国内研究进展很快,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共同发起建立了中华粪菌库紧急救援计划,又与天津大学联合研发了全球首套粪菌智能处理系统,实现粪菌的自动采集、分离和纯化,再经内镜或引流管将量化的菌液注射到患者的肠道内。脑肠相关学说等领域的新成果,大大拓展了研究范围,粪菌移植也引入到“整合肠病学”之中,还顺应了人们对粪便厌恶的心理。
同时,微生态制剂,如:培菲康(双歧杆菌、嗜酸乳酸杆菌和粪链球菌)、亿活(布拉氏酵母菌)、宝乐安(酪酸梭菌)、整肠生(地衣芽胞杆菌)等,都在临床得到了广泛使用,儿科则用于急慢性腹泻、便秘、再发性腹痛、肠系膜淋巴结炎、鹅口疮、夜啼、厌食、新生儿黄疸,等等。正如20年前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魏曦教授所预言的那样:“光辉的抗生素时代之后必将出现一个微生态制剂的时代。”
中医药学是伟大的宝库。科学研究应慎做“三季人”。许多看似“不科学”的内容,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认知的不断提高,会逐步揭示出科学的内涵,更好地为防病治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