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乡医路(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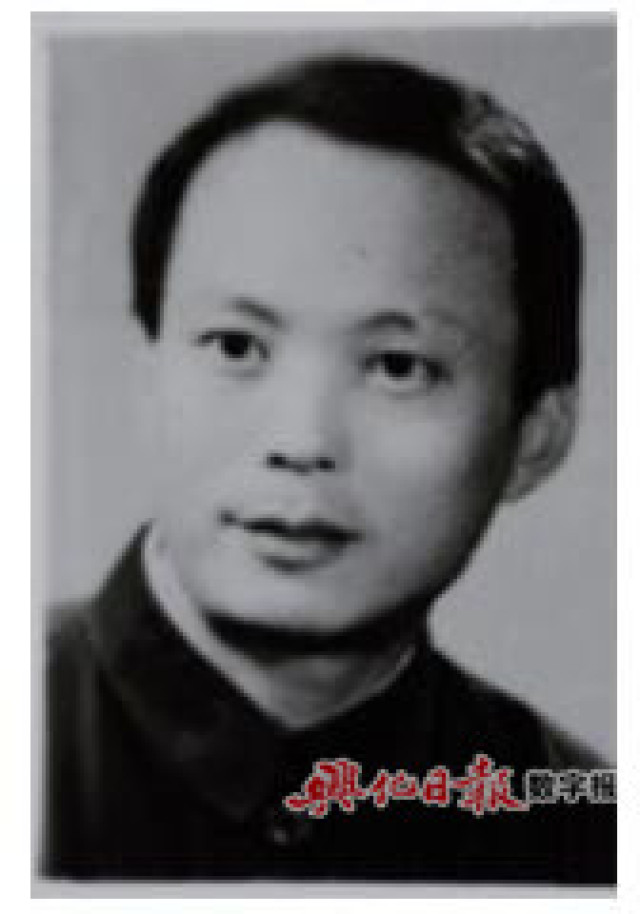
■/赵家定
乡医生涯
1964年4月26日,县卫生局安排我到李健区山子公社卫生所工作,同年12月31日又被调到荡朱公社卫生所工作,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李健区有12个小公社,公社卫生所工作条件都很差,一般有3至4个医护人员,我所在的荡朱公社卫生所连桌椅和常用的药品等资产仅600元,但却承担着全公社一万多人的防治任务。荡朱庄离县城水路15 里,交通不便,来往全靠船、竹篙、双浆或摇橹。加之农民经济困难,除非重病,一般常见病都在当地就医。而当时的农村医生大多是师带徒出身,没有接受过系统医学教育,缺医少药情况相当严重。我们这些中专毕业的年轻医生就成了农村医院的医疗骨干。就这样,我们在十分简陋的医疗条件下没日没夜地工作起来。
1965年春,流脑仍在大流行,为响应县卫生局“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号召,我和药房的黄老先生留守卫生所过年。大年夜刚准备吃午饭,从圩岸大队送来一名高热、昏迷、呕吐、全身皮肤大片紫斑的20岁左右的男病人。这时的我虽工作才一年多,但对流脑的诊治已十分熟练。经检查确诊为暴发性流行性脑膜炎(即华弗氏综合症),这放在今天的医院也是一个惊动全科乃至全院的危重病人。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腾下自己的床铺给病人住,单枪匹马就给他用药输液治疗,陪伴着患者度过了春节,终于使患者转危为安,痊愈出院。
当年春天,我们公社卫生所还执行上级“流脑就地隔离治疗”的指示,借用荡朱庄的几间空房子办起了流脑简易病房,用稻草打地铺做病床。我和另外一个医生和这些急性传染病病人24小时吃住治疗共处一室,无法隔离、没有任何保护,全凭自己的青春活力与病魔抗争,救治了几十个危重病人,顺利完成了流脑收治任务。
在医疗条件简陋、交通不便的农村卫生所工作,肩上的担子很重,“大小内外喉、带看猪马牛”是对当年农村医生工作的真实写照。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郭兴庄一个高热、昏迷几天的妇女被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需转送县人民医院治疗。当时大河封冻,通往县城的全是泥泞的乡间小道,路滑难行。我负责护送病人,病家请了8个大劳力,用门板、竹杠、绳索做担架,顶风冒雪抬送病人。遇到圩坝口中独木桥,因风大桥滑,我们是爬着过桥,终于把病人安全地送到了县医院。因为农民们没有粮票买吃的,我把身上的粮票全给了他们,回家一看,廿多里的路程把刚穿上脚的一双新袜子全磨破了。像这样护送病人、包括夜间出诊,当时都是不收费义务性服务。徐官庄一个产后高热的患者,也因雨雪、天寒地冻不能来诊所就医,我随来人到患家出诊,住宿在患家厨房地铺上三天,直到病人热退。离开病家前,我把三天的伙食费、粮票交给病人家属,这对于在当时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不准多吃多占的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有一次,一个小孩把一颗豆子塞进了鼻孔,抱来急诊。经检查豆子在鼻腔深处,小儿不停哭闹,无法硬取,我用手轻按无异物的一侧鼻腔,用嘴巴紧贴小儿嘴巴用力一吹,豆子从患儿鼻腔深处像子弹一样射了出来。至于农村大忙,顶风冒雨背着药箱走村串巷送医上门,为病猪打针开刀放脓更是家常便饭。而深更半夜,我听见巷道内急促的脚步声,就警觉起来,一听到叫门声即应声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