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少年
梦回少年
——读庞余亮《顽童驯师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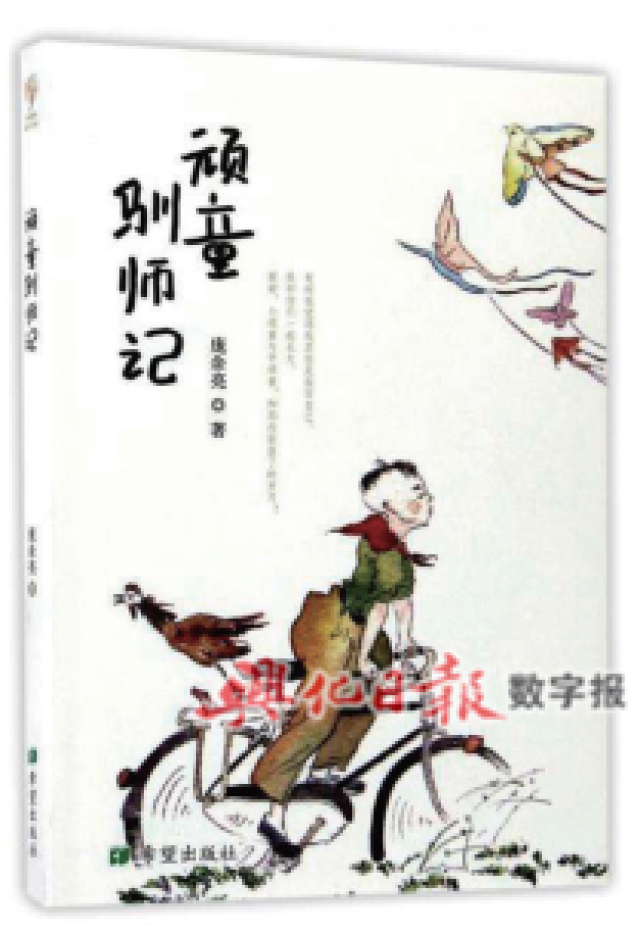
□孙爱雪
去年8月,我收到庞余亮老师的新书《顽童驯师记》。整个秋天,以及秋天之后的日子,每天都在无序的奔忙中疲惫不堪,而身后又仿佛时刻有鞭子高扬着,被追赶着、逼迫着,越发手忙脚乱,许多书都无暇顾忌阅读。无论日子多么仓促,我一直惦记着这本《顽童驯师记》,我要等一个安静的时间,认真阅读。
当我捧起这本书,一个章节一个章节读下去的时候,我又有了久违的手不释卷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如此美好。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独立成篇,但我没有把它们当作单篇的文章去读,我把它当做一个连续的大故事去读,读完一个小故事急不可待地去读下一个,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直到最后一个字,我还想继续往下翻书。书已读完,我意犹未尽,觉着那些故事,那些乡村学校里的小先生和少年们成长中的趣事还会有很多很多,可是作家说:“青草芬芳,顽童长大”,“就在那个秋天,我原谅了所有的顽童,也原谅了自己”。作家已说结束语,我还不能走出书中的情愫。犹如观影,大屏幕徐徐拉上,我还意犹未尽。
读《顽童驯师记》就是和书中的顽童们一起重回了一次校园。是的,是再一次回到校园,回到趣味盎然的少年时代。乡村的学校大同小异,乡村顽童们的趣事有着太多惊人的相似,乡村先生们的智慧又是怎样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的呢?读书中的章节,仿佛不是发生在庞余亮老师的沙沟,而是在写我的校园,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们。从第一篇《偷偷打钟的少年》我就嗅到了我少年时的气息,我们这里那些鬼头鬼脑男生也总是想偷偷地去敲钟,敲到钟的少年充满得意和胜利,听自己敲响的钟声传出悠扬的声音,少年一脸陶醉。学生喊老师的名字,在树上刻老师的名字,我们也干过,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还会在路边写老师的名字,给讲课声音高的老师起一个“大喇叭”的外号。成长的过程匪夷所思,孩子的顽劣啊,真是岂有此理!无论哪一个地方的小猴子、小老鼠们,都是一样顽劣。其实,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这样淘气过来的呢?
那么多年过去了,作为学生的我们,可着劲淘气、顽皮,从来没有想过老师们是怎么想我们的,在《顽童驯师记》里,我看到了十八岁的小先生好奇又机智,生气又宽容,和顽童们比智谋比耐心比小小的狡计,而更多的是温厚,是疼爱,是呵护。他会不动声色地捉住晃动光圈的学生,还要忍耐那只放屁虫和少年们的幸灾乐祸。他应声而答少年的呼喊,喊老师名字的少年一听到老师答应,就立刻噤声了。小先生的机智和幽默,少年心里一定怯怯的,又暖暖的。他知道学生在树上刻自己的名字,没有去查找那个学生,没有去想批评那个学生,他有些好奇,到树上去找自己的名字。小先生对那个刻在树上的名字饶有兴趣。兴趣归兴趣,小先生更多是对顽童们的宽容。
在书里,我遇到了曾经的自己,似曾相似的画面如此亲切,遗失在记忆深处的小游戏重新复活,那是真正的游戏,天然的、散发着碎银子一样光泽的游戏。如“挤暖和”,我们热烈地玩过,叫“挤香油”。我做过泥哨,也快乐地吹过泥哨。春天或者夏天,谁不做几只泥哨边走边吹呢?还会随手摘下树叶,放在嘴上吹出各种声音。《五种泥活秘诀》中的泥惯炮,我们叫摔瓦屋,做法一样玩法一样,最后的惩罚有一点小区别。我们也是做成碗状,还要唱“瓦屋楼,响不响?!”对方答:响!话落处啪一声摔地下,炸开花,摔出一个大洞。我们不喊输家“厚脸”,我们罚输家拿出足够的胶泥,去补开花的洞口,输家会把胶泥做成薄薄的一片贴在洞口上。小老鼠们的“咬时”和我们二月二吃“蝎子爪”一样,是异曲同工,他们咬的是炒蚕豆,我们咬的是炒黄豆,“那时校园里都像是有一群小老鼠在磨牙。炒蚕豆的芳香就这么溢满了我的肺腑”。我们的男老师会坐在进教师的门边拦住学生,挨个讨要学生的“蝎子爪”,三粒五粒,老师和少年们都咯嘣咯嘣地咬得豆香四溢。女老师的寝室和讲桌上,女生们会偷偷地送过去。小先生和少年们烤知了,我们也在夏夜点起火光,火光中知了啪啪地从树上掉下来。也会用麦子在嘴里嚼黏性很强的面筋去粘知了——这些沉潜在记忆深处的片段一一打捞上来,它们带着岁月的芬芳在这本书里散发着沉淀之后的醇香,阅读的愉快油然而生,电影一样的画面浮现,不时露出会心一笑,有时又为少年们天然去雕饰的顽皮深深感动。
《顽童驯师记》是写小先生和少年学生一起成长的故事,又是成年人写给少年人的书,作家带着成年后的深情回望那段青涩岁月,对顽童们成长的经历多了悲悯,多了沉重的思索。也或许作家在做小先生的时候,就已经在心里有了忧伤和悲悯的情结。长辫子的女生有心脏病,小先生不让她值日、不让她做广播操、不让她参加集体劳动,医生说她只能活到20岁,小先生心疼这个嘴唇发紫浑身哆嗦的孩子,他能做的也只有减少她的体力劳动。《乡村百合》和《栀子花开》都是写失学乡村女生的,“我教过的学生中途辍学回家的男孩很少,几乎清一色女孩”。她们短暂的学生生活让小先生“心里忧伤起来。班里又有两名女生失学了。每年都是这样,让我的心空出一块”。乡村女孩成长的过程有了障碍,失学是一个孩子命运的拐点,小小少年在人生还没有开始就遭遇到命运的不公平,小先生心里空了,他无处安放的心变得沉重,因为这些乡村少年没有学上。小先生在路上遇到干完农活回来的女孩子,她们满脸通红地与老师擦肩而过“像一阵忧郁的风,吹得我的心一点也不能轻松起来”。
简陋的乡村学校,没有围墙,苦楝树、刺槐或梧桐充当围墙,村子里的猪羊狗、鸡鸭鹅、麻雀、兔子、癞蛤蟆等等都在教室外当旁听生听课,害得校长把一只鸡追得飞到屋顶上。小先生在这个乡村学校里偶尔也会有些苦闷的,他写了《苦闷的夏天》也写了《那个多云的下午》,苦闷中的小先生想离开学校“我面前好像有很多去路,实际我没有一条路敢走”“有时候,我就走出屋外,想想自己的命运,总是想得头疼。我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正散落在大地某处纳凉和做梦的少年们”。《那个多云的下午》校长说小先生有点忧郁。为了让小先生开心,校长知道课代表被同学画了一张鬼脸,他不说,小先生看着认真听讲的课代表,开心地笑了“那个多云的下午,我的心情非常愉悦”。善于观察的校长和老先生们爱护着肚子里装满墨水的小先生呢。
乡村学校——这个教人成长的地方,大地上最深沉的最厚实的地方,虽条件艰苦,小先生和少年们在这里享受成长的快乐。寂静的夜里,家访归来的小先生能听到月亮的笑声,而刷了白灰的树被少年们想象成“树穿了白球鞋”。下雪了,严厉的校长也童真了一次,和孩子们一起蹬树上的雪。小先生还会学着顽童的样子爬上草垛顶,“孩子们滑着草垛,我也觉得我的内心有一块快乐之蜜往下淌,单调的乡村生活,对于清澈的孩子,如一滴水一样并不单调”。
读《顽童驯师记》,我梦回少年,杂芜的心变得单纯快乐。感谢庞余亮老师的书写,让我们回归童真,捡拾到成长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