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死亡的死亡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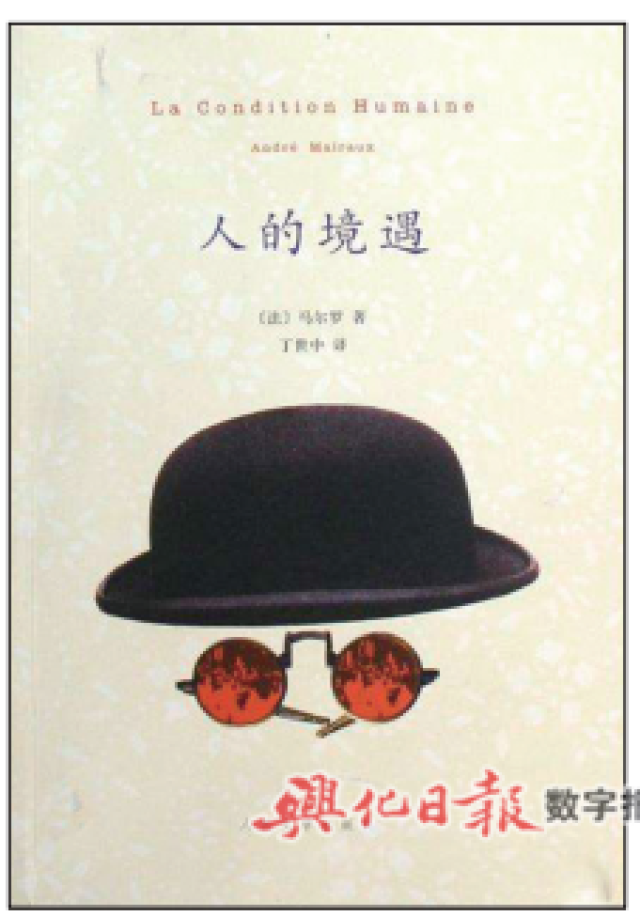
□易 康
1933年对于不同寻常的安德烈·马尔罗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他的母亲病故,女儿诞生;他采访托洛茨基,发表反法西斯演说;他成为尚不被看好的福克纳的拥趸者,为其颇受争议的《圣殿》法文版作序。更不寻常的,是他发表出版了《人的境遇》,该书为他赢得了龚古尔文学奖,从此马尔罗便跻身于法国一流大作家的行列。
《人的境遇》以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题材,描写了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冲突。这部本应引起中国读者阅读兴趣的作品,却没有产生大的反响。在中国,马尔罗的知名度不仅不及萨特、加缪,而且不如“新小说”和“新寓言”派,这和他在自己的祖国所获得的各种殊荣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其原因恐怕是人们把他看成一个半吊子政治小说家,或者是一个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历史事实的历史小说家。
尼赞说过:死亡是马尔罗作品中的重要主题。读过《人的境遇》的中国读者可以对书中关于中国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述不以为然,甚至是嗤之以鼻,但他们却不可能忽略这部小说中连篇累牍的死亡描述,因为这种描述远比那些历史事件的描述更令人触目惊心。马尔罗纵然不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小说家,也应该是一个以描述死亡为能事的好手。
翻开小说的第一个章节,人们就开始接触这种描述。革命者陈刺杀一名军火中间商,得手之后,“他兀自面对死亡、单独地呆在一片无人之地,被恐怖血腥压迫得颓然乏力”。接着马尔罗叙述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情形,起义军民合力围攻一列军阀部队的装甲列车,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调来火炮增援:“又出现一片沉浊的铁器轰鸣声,那是革命军的炮火。每片装甲都遮掩着一个车中人,他们聆听这轰鸣声就像听见死神光临一般。”在此,令读者感触良深的与其说是死亡本身的恐怖,还不如说是被动等待死亡的恐怖。
在国民党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以后,陈决定刺杀蒋介石。他抱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专车,“(陈)闯进一个亮得刺眼的圆球中。他的上衣不见了,右手拿着一块沾满污泥和鲜血的车篷残片……他想摸裤兜,没了裤子,连腿也没有了,只剩下炸碎的肉”。陈最后用自戕结束了死前痛苦的挣扎,他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地走向死亡。与陈的强悍形成对照的是侨居上海的比利时“小人物”赫梅尔里克,陈牺牲后,赫梅尔里克的唱片铺遭到国民党军的洗劫,妻儿被杀害。“他夺门而入:满地是破碎凌乱的唱片,夹着大块大块的血迹……‘但愿他们已经断气!’赫梅尔里克想。他最怕眼见他们垂死挣扎。”此后,懦弱的赫梅尔里克开始抗争,他不甘坐以待毙,最终在与国民党军的巷战中死里逃生。“黑影正在渐渐缩短,看看它们就可以不去想那些要死去的人。像日复一日的情形一样,它们正以永恒的运动收缩着自身,今天更显示出一种粗犷的庄严,因为这些人将永不能再见到这种运动”。赫梅尔里克最终还是“再见到这种运动”,因为他行动了,他的拼死一挣使自己摆脱了被动等待的命运,也为自己在绝境中求得了一条生路。
通读了《人的境遇》的人们发现,马尔罗描述至此,还仅仅是“热身”,真正令人恐惧的死亡境遇是发生在强矢和加托夫这两个人物身上。他们都共产党领导人,被捕后被刽子手归为“甲类”处置,即扔进机车锅炉里活活烧死:“一种尖啸声腾空而起,压住细语与呻吟,那是来自一部火车头的尖啸声”。强矢在行刑之前服下了氰化物,“他始终认为:按自己的方式去死是美好的,那便是酷如其生的死”。强矢咽气后,加托夫深感孤单,“当人们不是独自去死时,死是容易的”,然而在最后一刻,加托夫却将氰化物赠给了两个年轻的战友,使他们免受酷刑的折磨,然后独自挺身走向残酷的死亡,“得啦,就算我死于一场火灾吧。”“死可以成为一种充满激情的行动,成为生的最高表现,而这生与死又何其相酷似。”
综上所述,人们不难发现马尔罗这部小说里有关死亡描述的线索:感受——选择——抗拒。陈和强矢都是自寻死路,他们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各自用自己的方式了结生命。赫梅尔里克死中求生,用行动抗拒了死亡。而加托夫则把摆脱痛苦机会留给了别人,凛然受酷刑而死,最终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他虽然放弃了选择死亡的方式,却在陈和强矢超越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超越。
众所周知,马尔罗深受帕斯卡思想的影响,认同其关于人的生存荒谬的阐述。他认为:人应该争取、对抗、行动,以此来战胜、对抗荒谬,以寻找人类生存的意义,恢复人的尊严。由此可知,在这部充斥着死亡描述的小说里,马尔罗实质上是在阐述人应该如何摆脱宿命,超越死亡,抗拒荒谬。他的这种表述,对以后的萨特、加缪、圣埃克苏佩里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这么说,《人的境遇》为法国现当代文学确立了一个新的命题。
当一些中国读者还在为这部小说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而纠结不清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对作品的错误解读;当一些学者还在盛赞马尔罗如何对中国政治充满多么高的热情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在买椟还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