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场顺流而下的哑剧
人生是一场顺流而下的哑剧
——读《有的人》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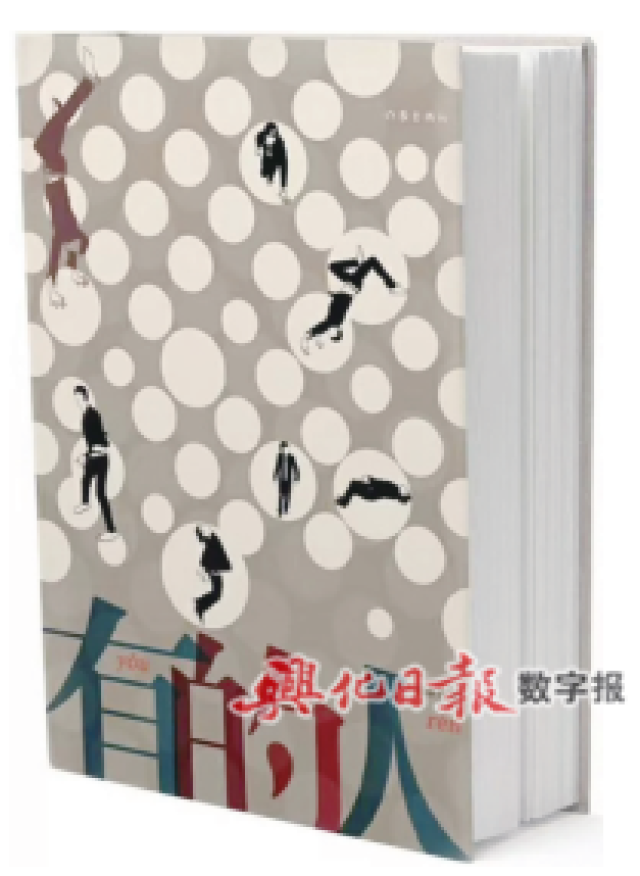
□闻 琴
坦白说,虽然是名作家的作品,但《有的人》阅读起来并不流畅,有些文字似乎能一跳而过,有的文字却必须来来回回地读,反复地看,逐字逐句地斟酌,字字跳击心脏。很累,很沉闷、压抑。每段章节都像一颗珍珠,但是散发的光芒程度不同,有的闪亮;有的晦涩;有的晶莹欲滴;有的嵌进泥土,阴冷暗沉得只想丢出几声看透世情的“讽笑”。
看完《有的人》,我仿佛看到作者在改完最后一章后,起身、挪位、关闭电脑,伸一个长长的懒腰,喝几口茶,然后对自己冷静地自言自语:结束了。写完了,就放下了,结束了。书中的人物生活还在继续,但“我”的人生终究不同。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经历过文字的反刍,“我”的心已经得到涤荡洗礼,或者说得到了暂时的安宁妥协,更何况,“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不管失去多少,对待生活,“我”永远是朝前看的。
诚如作家所说,这是一部中年人的妥协史,一个父亲的心灵成长史。“妥协”是我看到的最最痛苦的字眼。万事万物,不到万不得已,何谈妥协?妥协,意味着选择、牺牲、包容、无原则的退让。彭三郎的人生一直在妥协,他的底线一直在放宽,放宽到连最后的一点精神自留地——诗歌,也将离他而去。和大多数男人一样,彭三郎渴望金钱,渴望女人,也出过轨,在出世和入世间徘徊彷徨,既想超脱什么都不管,可又为了现实自愿低到尘埃里去。他是矛盾的、痛苦的、纠结的、失落的;同时也是清醒的、善良的、有底线的;所以他最终选择对生活,妥协了。妥协的这一刻,他的心又恢复了宁静,也黯然地圆融了,并以此赞美儿子是福将,妻子张荞麦是福将的妈妈。这是他对还没熄火的家庭的希望,也是他在这场持久战中身心疲惫的唯一获利品。
读者欣喜地看到,文章开头和结尾是能够画一个圆圈的。生活本就是一个圈。不管跋涉了多少路程,人最终还是要回家。这是无奈,是宿命,是一场已经布好的局,是想要说话却又张不出口的哑剧。有多少人,被迫地、无奈地、顺从地,在生活的闹剧中,甘当明了一切的哑巴。
《有的人》归根溯源,更应该追究原生家庭对一个人一生的重要影响力。主人公彭三郎于外人看,虽然在条件艰苦的农村长大,但受过正规教育,仕途顺利,是很多村人羡慕的对象。那个年代,一个读过书的“公家人”,是有地位的。但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生活的艰苦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有时还是回忆的乐趣,是写稿的灵感来源。而心灵的磨难才真正让他喘不过气来。这个磨难的源头,是把他带到世上的父亲。父亲,这个沉重闪耀黑斑的字眼,在文中上下前后多次出现。他像一团黑色的云,总是在彭三郎觉得忘记了他的存在时,又黑压压地笼罩过来。
主人公对父亲的恨意,似乎与生俱来。午夜梦回,总是挥之不去。毫无疑问,父亲,在彭三郎的人生中,占据了绝对的主角地位,影响了他整个的童年,甚至是青年、盛年。父亲对母亲的殴打,父亲的出轨,父亲的粗鲁,一直是彭三郎的噩梦。严格地说,彭三郎就是一个缺乏父亲引导的孩子。他在叛逆和质疑中成长。每质疑一次(得到了赞同),就加重一次鄙夷。父亲屡次赞美夭折的彭二郎,也更让彭三郎在潜意识中下定决定要超过他。这让我怀疑,是否从此以后,彭三郎以彭二郎当作自己人生的竞争者,发誓要出人头地,夺得父亲的赞美。又抑或是将自己作为彭二郎的替身?说到底,彭三郎就是一个缺乏赞美的自卑孩子。他需要肯定,从父亲的眼睛中,从村人的目光中,从读书中,从诗歌中……
父亲是什么?是比我们先来到世上的人。主人公对父亲是鄙夷的、愤怒的、不屑的。父亲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撒了一把种子,只是给了我们比牲畜好一点的生活,就可以昂扬在整个家庭的头上,作威作福。但是妻子和孩子必须得感恩,就得什么都听他的派遣。父亲?他配叫父亲吗?少年、青年、中年的彭三郎一直在质问。可他发现,自己越讨厌什么人,也就越变成什么人。他出轨了。他认为这是彭家基因的遗传。他对儿子不那么上心,因为潜意识中,他的少年时代,父亲也是这样对他的。在文章快要结尾的时候,主人公有大段大段心灵的独白,那是控诉,是反刍,是对自己和父亲这一段关系的交待。不管好歹,不管结果,明知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作者还是执拗地要给一个交待。要不,他的灵魂不安静。就像他回忆给父亲置办丧事,没买到一双合适的小白鞋,王三四建议他用一块白色的胶带代替。只是代替,用这种借代的方式,他也要强迫自己获得心灵的宁静。
父亲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他给予彭三郎,大多是痛苦的回忆。农村中的父亲大抵就是这样,粗糙、直接、蛮横、狡猾,崇拜功名、见风使舵。文中第161页,主人公从师范毕业回来,丢了派遣证,父亲没有大声呵斥他,说话温柔了,还买来猪蹄,在主人公睡觉的床前,用尖锐的镊子剃毛。这是一个温馨的场面。在这里,父亲显示了对彭三郎的关心。但我又疑惑,倘若彭三郎没有去读书,初中毕业就在家务农,或者在附近工厂打工,生病了,父亲还会这样对他吗?父亲爱的不是儿子,而是具有公家人身份的儿子。他爱儿子能给他带来荣耀,能让他挺起腰板在村里说话。这种观念,一直到父亲去世还是根深蒂固。
小说通过一章章的断片似的描写,描写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具有雷同的身份——父亲。父亲是一枚纽扣,可以交叉不同人的人生。小说抽丝剥茧,一层一层地,剥出一个又一个内核,不管是“我”的文学梦,“我”下乡的挂职锻炼,朋友陈皮的死,以及“我”和情人白若君之间的纠葛,还有家庭中的琐碎……最终,赫然地,都会冒出一两句父亲的描写。他时而狰狞出现,时而露出神秘的笑容,时而带有善意的劝告,时而又站在壁上沉默寡言。
父亲,始终是作者深层次的情感皈依。人在精神上总要有一个支柱的。不是爱情,就是亲情。即使这亲情并不圆满,残迹斑斑。主人公坚定认为,父亲是有罪的。不是针对某个个体,而是统称。只要是当父亲的人,都有罪。主人公有了儿子,他也是沿着父亲的“有罪”结论,开启自己的父亲之旅。一面批判,一面审视;一面反刍,一面汲取。这是人性的悲哀,但这就是人生,充满了瑕疵的、可笑的、矛盾的、龌蹉的人生。正因为父亲是不合格的,所以彭三郎最后丢弃了那些诱惑,心甘情愿地在自己的小圈圈里日复一日地过日子。为了当好丈夫,当好父亲,他妥协了,也成长了,人生也就丰盈了。彭三郎是带着眼泪微笑的,或是带着微笑掉泪的。但不管怎样,只要微笑还在,生活就还得继续。
文中后记,作家还是意犹未尽,可能感触太深吧。既然都已笔落成字了,那就干脆不遗余留地宣泄个痛快吧。他拿歌手周杰伦的父亲做例子。周出身离异家庭,很早父母离异,周杰伦对父亲的记忆就是殴打母亲,冷漠,出轨。所以,他恨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杰伦拒绝在公众场合提起父亲。周父是初中物理老师。成名后,周父打破壁垒,也来看望他。周杰伦邀请父亲在自己的电影中加盟,让他客串一个生物学老师的角色,也是讽刺。
每个人都是被迫出生到这世上的,婴儿永远以响亮的啼哭迎接这个世界。我们不欠父亲的,父亲欠我们的。这一欠,就是一辈子。绝大多数父亲意识不到自己的过错,他们得意洋洋,他们性情暴躁,他们高高在上,他们是一家之主,对着妻儿为所欲为,凌驾他们之上。(父亲的火车锈迹斑斑,制度的铁轨永远锃亮。)如何打倒父亲?攻击父亲?如何让他们低下烦躁的头颅?如何让父亲和我们人格平等,平等地对话,互相指出彼此的不对,推心置腹地聊天,而不是压以孝字的名义,去恭敬、顺从?这需要法律的帮助,道德的宽宏,观念的改变。
可是人都会老的,父亲也一样,只要被称之为父亲的都有老去的那一天。如果不存悲悯之心,那世上绝大多数人将活在怨憎中,为家务琐事,终日吵闹。人性本恶,人性就是不完美的。那父亲也是不完美的。宽恕父亲,就是宽恕自己。反刍父亲,就是反刍自己。如果父亲是一出滑稽的哑剧,那自己有一天也要接着上演,承前启后地演,佯装入戏地演。感动了别人,或许也就感动了自己吧。
《有的人》这本书很沉重,这区别作家的其他作品。读罢,有十年珠玑字字滴血之感。这是作家本人将在漫长岁月中的苦痛磨砺成了光华的珍珠,将时光的点点滴滴封存成了化石,将那些美的丑的唾弃的感动的光明的阴暗的,一一剥去伪装,坦荡地、豪迈地,放在台面上,供人品评。值得尊敬,值得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