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弓腰的样子,也是它的骄傲”
“它弓腰的样子,也是它的骄傲”
——谈庞余亮《报母亲大人书》中的“弯腰”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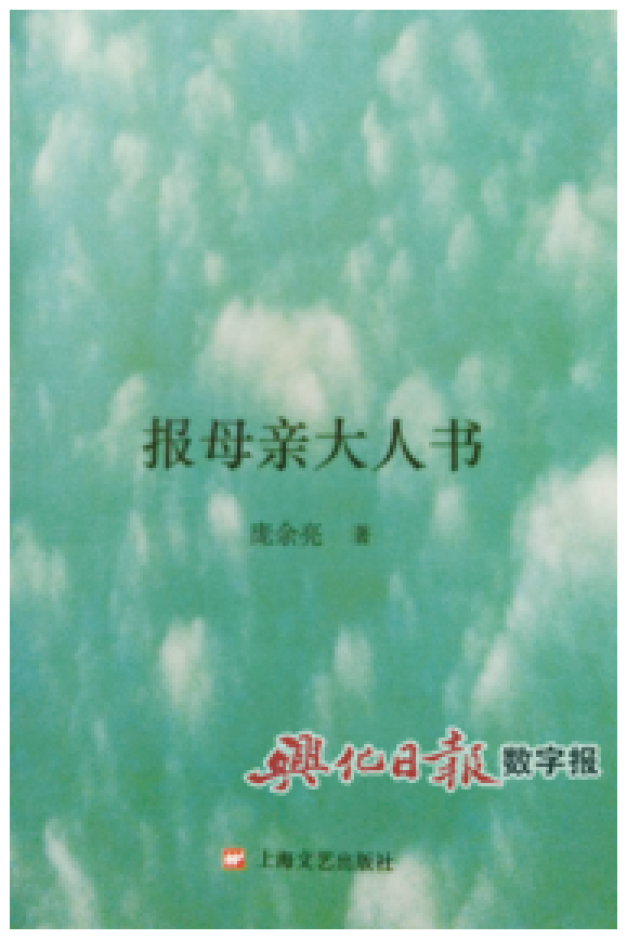
□罗安斌
一说起庞余亮,还是会想起那句著名的诗:“春天,十个海子在复活”。庞余亮多年来的创作,从诗歌到童话,从散文到小说,也表现出如“十个海子”一样的丰富性:繁复而灵巧的象征隐喻体系、多变而精致的结构、沉郁而不失雄浑的主题……。但在这丰富性的背后,有一些恒常性的东西一直在闪耀,乃至贯串了其所有文体的创作过程。翻开其新近出版的诗集《报母亲大人书》,我们同样发现了这种恒常性的延续和进化。这本集子中,有一首《清明桥之夜》特别值得注意:
这叫清明桥
这叫古运河
这叫水弄堂
暗自上涨的水令船头逼仄
必须躬身过桥
就如必须躬身
向破碎的亘古长夜致敬
对庞余亮的作品熟悉的读者读到此处不能不想起他早年的几首诗:《弯腰拾麦》《弯曲下来》和《谦卑把我取名为向日葵》。在《弯腰拾麦》中,作者歌颂了“弯腰”的劳动美学和皈依大地的满足感。像米勒《拾穗者》油画一样,画面充满了金色的希望:总有一束阳光,打在那排英俊的白杨树上。而在《弯曲下来》和《谦卑把我取名为向日葵》等诗中,“弯腰低头”则是表达了对沉重的生活和苦难底层的敬意,表达了作者和其抒情对象一致的谦卑感:我常年劳作/不仅是常年劳作/我是习惯了我内心的向日葵。自古以来,中国诗歌和诗人从诗经到汉乐府,从杜甫到陆游,面对民间疾苦,少有这样的谦卑感,而是抱着同情怜悯的心态。直到“五四”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诗人,才愿意低头亲吻农夫脚上的泥土。但早年的这些白话诗人,往往出身于士绅家庭,对于民间和底层,往往只有理念上亲近而无身同感受的谦卑,这和当代一些如庞余亮一样起于草根的诗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清明桥》中,弯腰“致敬”还在,但是所致敬的对象发生了根本变化。“亘古长夜”完全不同于沉重苦难的生活,它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宿命性和邪恶性。从这首诗中,我们再也看不到打在英俊白杨树上的那束阳光了。其实,对于现实的种种苦难,对于“铅笔芯中的黑”,作者一直通过一种“致敬”和“宽恕”精神来控制和把握:“为了宽恕它,我们砍下了整整一座疼痛的苹果园”。某种程度上,宽恕就是隐忍,宽恕就是退却。可是正如作者在《车技》中描述的退却一样,从“大卡车”退成“小汽车”、又从“小汽车”退成“自行车”,再从小汽车退成“独轮车”时,往往退无可退,作者在生活中表演着“平衡术”,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极端苦难,是一种退无可退的悲剧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无法从“致敬”和“谦卑”中得到解脱,而生命的意义也越来越轻,越来越渺微。因此可以说,《清明桥》中的“弓腰”意象,从乐观精神上讲,作者是在退却;但是从对生命意义思考的角度看,作者是在升华和掘进。读这首诗,甚至让我们想到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某种意境。
“弯腰”“折腰”这些意象,在中国古诗意象中屡见不鲜,但基本上都和表达知识分子和英雄生命的风骨有关。而真正开发出这个意象的丰富意蕴的,庞余亮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报母亲大人书》中,作者不止一次写到了疼痛的椎间盘。而《草》这首诗写道:
他们踩着草远去
一些草被踩得弯下腰去
一些草也就慢慢挺起腰来
默默看着他们远去
又有一些人踩了过来
一些草又被踩得弯下腰去
一会儿它们还会挺起腰来
看着那些人走远的背影
皇天,光阴,马匹,野火
等一场大雨浇灭了滚滚红尘
是我们站在那小道上伸头张望
与其说作者是在通过这首诗复活中国古诗中“风骨”传统和向鲁迅先生致敬,不如说是在复活作者身上一直存在的又曾被自己无情解构的英雄主义情怀。
也许对于庞余亮来说,生活和生命就是一组弯腰低头的剪影,而对于热爱他的读者来说,庞余亮的诗歌正如他笔下的那只老台灯:
它弓腰的样子
也是它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