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飞跎全传》作者邹必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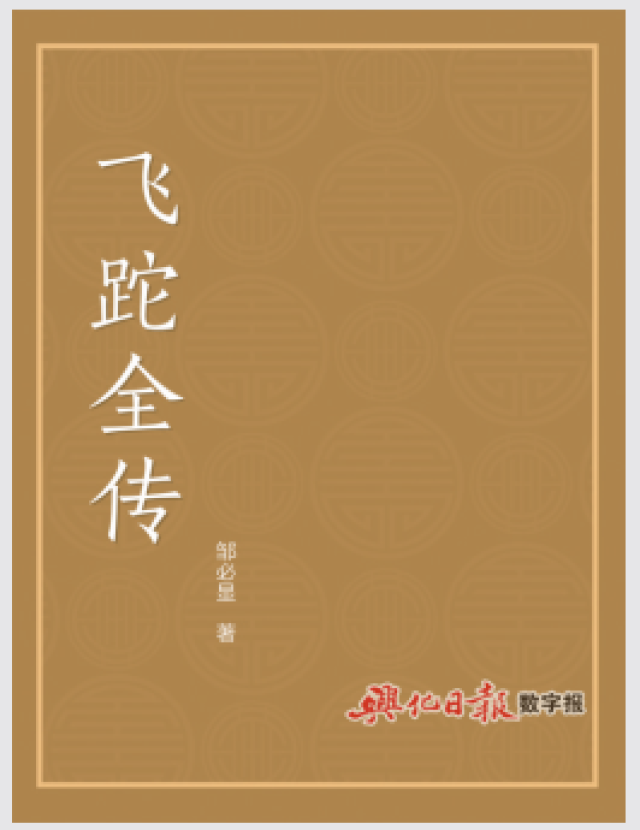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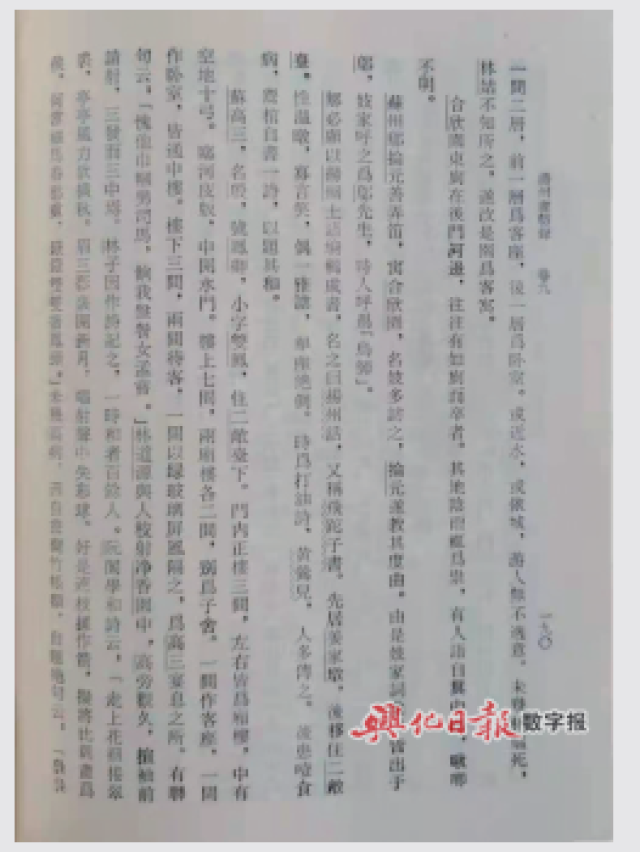

《飞跎全传》
《飞跎全传》插图
《扬州画舫录》中的邹必显简介
西门片规划中邹家祠堂巷“评话展示馆”
□文/任祖镛
《飞跎全传》又称《飞跎传》《飞跎子书》,共32回,4万2千余字,是评话底本,专讲飞跎子故事。“跎”本指“驼背”之人,而扬州方言的“飞跎”或“跳飞跎”,是指当时靠空手套白狼来诈骗钱财的市井之徒。阮元的舅父林苏门的《邗江三百吟》卷十《戏谑方言》中就有《飞跳跎子》一首,小序为:“无为而有,见人之财,以计跎而用之,曰‘跳飞跎子’。”诗云:“纵然赤手无凭藉,妙在空心好作为。莫说承蜩有疽瘘,让君能跳又能飞。”可见飞跎子擅长翻空心筋斗,做无本钱买卖;就像《庄子》中驼背老人能用竹竿粘捕高树上蝉一样,手段很高明。
《飞跎全传》的作者是兴化人邹必显,自号己趣斋主人,乾嘉时期评话艺术大师。
邹必显的祖辈邹荣一携弟荣二在明洪武七年(1374年)从苏州迁居兴化,定居西城外阳山里,成为范阳邹氏的迁兴始祖。此后兴化邹氏在西门外聚族而居,但读书未见显达,无人中进士。嘉靖年间出过一位举人邹充曾任知县,隆庆六年(1572)出过一位贡生,任州同(从六品),是知州的佐官;于明万历二年(1574)建成“邹氏宗祠”。至今兴化西门外仍有东、西邹家祠堂巷。邹必显在康熙末期出生于兴化西门外阳山里。他作为评话大师和话本小说的作者,当时在扬州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但评话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小说属稗官野史,不能登大雅之堂,因而他的生平事迹地方史志皆不载,只能在文人笔记中留下痕迹。
记载邹必显生平内容较多的是《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生于乾隆十四年(1749),为了完成这一本书,花费30多年搜集资料,书中保存了从康熙末期到乾隆时期的扬州重要人文史料,其中简要记载了《飞跎全传》作者邹必显和《清风闸》作者浦琳两位评话大师的生平。
扬州评话是继宋代话本之后平民文学的一次再兴起,明代后期至清代,成为扬州地域重要文化标志之一。清代扬州盐商聚集,高度繁荣,社会底层的广大平民也有了文化娱乐的需求,因而评话发展很快。它不同于戏剧,对表演场地要求不高;说书人无需配角,也无需演出的各种道具,只要一方醒木,还有折扇、茶壶即可。演出成本低,收费必然不多,能适合平民需要。《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就有评话场所的记载:
大东门书场在董子祠坡儿下厕房旁。四面团座,中设书台,门悬书招,上三字横写,为评话人姓名,下四字直写,曰“开讲书词”。屋主与评话以单双日相替敛钱,钱至一千者为名工,各门街巷皆有之。
我们平时都说“听书”,因到书场主要靠耳朵听,所以听众可四面围坐,中间台子上放着说书人的书桌,书桌前有绣花桌围,说书人穿长衫、握折扇居中高坐,显得儒雅体面。如果四面的听众有200人,每人5个铜钱,就可收到1000个铜钱,也就是一贯钱,书场的屋主和评话艺人每天可各得到500个铜钱,就很满意,这个说书人也就成为“名工”,被大家称赞;而这样的收费也是平民能承受的。当时扬州书场“各门街巷皆有之”,可见乾隆年间扬州评话已相当普及,书场多,必然说书艺人多,书目多;不仅扬州如此,所属各州县亦然。如兴化当时就有书场多家,其中在北小街东字桥南侧的裴福兴书场,大门朝西,迎门是茶炉,从两边进出,里边南北向三大间,靠东墙的中间是书台,听众分西、南、北三面坐,可容一百多人。这一书场从清代到民国,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生活在评话说书市场繁荣的当时,邹家弟子读书久不效,邹必显语言表达的天分又很高,走上说书之路并不奇怪。
《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中对邹必显的记载有两处,其一是:
邹必显以扬州土语编辑成书,名之曰《扬州话》,又称《飞砣子书》。先居姜家墩,后移住二敌台。性温暾,寡言笑,偶一雅谑,举座绝倒。时为打油诗、黄莺儿,人多传之。后患噎食病,鬻棺自书一诗,以题其和。
从中可见,他到扬州曾先后寓居在郊区姜家墩、二敌台。他性格有点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不过偶尔说句开玩笑的话,却高雅诙谐,十分有趣,能使所有在场的人前俯后仰地大笑不止。他能写打油诗和“黄莺儿”,被很多人欣赏,互相流传。因“黄莺儿”既是词牌名,又是曲牌名,这里的黄莺儿他是填的词还是写的曲,就难说清,但不论是词或曲,他的“黄莺儿”受到读者欢迎是肯定的。后来他得了“噎食病”,为了治病与生活,不得不卖掉准备百年之后用的棺柩,可见生活艰辛。至于“噎食病”有没有治好,文中没有交代。
这一段话就留下了两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是他大致的生卒年,二是《扬州话》与《飞跎子传》是同一本书还是两本书。
1.他的生卒年。
《扬州画舫录》成书的乾隆六十年(1795)之前,邹必显得了“噎食病”如果难以久活,可能在嘉庆初年就去世了。而现存《飞跎全传》前有一笑翁写的序,时间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序中说:“己趣斋主人负性英奇,寄情诗酒,往往乘醉放舟,与诸同人袭曼倩之诙谐,学庄周之隐语。一时闻者,无不哑然失笑。此《飞跎全传》之所以作也,书为同人欣赏,久请付梓,而主人终以游戏所成,惟恐受嗤俗目,不敢问世。昨因坊请甚殷,乃掀髯大噱曰:红尘鹿鹿,触绪增愁,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不独余悼之戚之。苟得是编而览焉,非拍案以狂呼,即抚膺而叫绝。若徒谓灵心慧舌,变化神奇,亦壮夫之所不为,岂有心无道之所乱容求媚者哉。余故与主人之刻是传,即书其所言,如此是为序。”
从序文可见,邹必显喝醉酒乘船游览,和同船的朋友说话非常有趣,他的话能像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字曼倩)那样诙谐滑稽,还能学庄子不把要说的意思直接说出来,而借用别的话表示,让大家去猜其中的含义,使人听了就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可见他所说的诙谐滑稽话有文学修养,内涵高雅,并非粗俗硬逗,这与《扬州画舫录》中说他“偶一雅谑,举座绝倒”完全一致。他写的《飞跎全传》被同行业的说书人欣赏,一直请他刻印成书,他担心被世俗人讥笑,不愿付印。直到刻书的商人多次恳请,他才掀开长长的胡须大笑说,如果得到这本书看后(明白作者所写的意思),一定能拍案叫绝;如果认为只是语言生动,情节有趣,这就不是写这本书的目的了。从一笑翁记下邹必显说的话作为序可推想,嘉庆二十二年(1817)邹必显还活着,去世当在嘉庆二十二年之后。而这与李斗所记内容并不矛盾,他的“噎食病”必然治好了,又活了20多年。
至于他的出生年代,乾隆五年(1740)郑板桥作序的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中,记有邹必显说书之事:“空心筋斗会腾挪,吃饭穿衣此辈多;倒树寻根邹必显,当场何苦说‘飞跎’。”董伟业是流寓扬州的沈阳诗人,作《扬州竹枝词》99首,自号“董竹枝”。这首诗可见,乾隆五年之前邹必显说《飞跎传》在扬州已出名,话本小说《飞跎传》本是说书人的底本,因而成书当在乾隆初年。他即使在扬州成名较早,也得20岁左右吧,这样推算,他可能出生在康熙末期(1720-1722),到嘉庆二十二年已90多岁,是一个高寿的作者了。
2.《扬州话》与《飞跎子书》是同一本书还是两本书?
《扬州画舫录》中说“邹必显以扬州土语编辑成书,名之曰《扬州话》,又称《飞砣子书》。”显然李斗说的是同一本书,属一书二名。
而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还有一段当时扬州十位评话大师的记载:“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诸人……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跎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这十位在扬州独步一时的“郡中称绝技者”中,有邹必显《飞跎传》、谎陈四《扬州话》,却把《飞跎传》和《扬州话》分为两部书,已不是一书二名了。遗憾的是现在《扬州话》已难寻觅,我们无法把二者作比较。而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中还有谎陈四学百鸟声的记载,有会口技的长处。可能邹必显开始学习说评话是用的《扬州话》的话本,飞跎子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邹必显在此基础上,增补了扬州市井人物和市井生活内容,整理加工成单独的《飞跎全传》评话脚本,李斗说他“编辑成书”可能是指这一点,所以《扬州话》与《飞跎子书》在邹必显说书的前期并无区别,二者属一书两名;其后,因他增补了大量的飞跎内容,就以说《飞跎全传》而成名,并被同人欣赏而“久请付梓”,显然同行已公认他是《飞跎传》的作者,否则就不必要他同意才“付梓”。至于后来谎陈四说的《扬州话》,当是经他加工过的本子,其中可能已无飞跎的内容,所以李斗分开表述,二者也不矛盾。
今年在我市西门片保护整治规划中,邹家祠堂巷内要建“平话展示馆”,形成“平话景观节点”,可与泰州评话大师柳敬亭的柳园呼应。以后,兴化人对这位清代乡贤的认识也会加深。













